
红土达坂是G219的最高点,海拔5380米。

云雾缭绕,乃村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远山如黛,湖岸芳草萋萋,野驴三五成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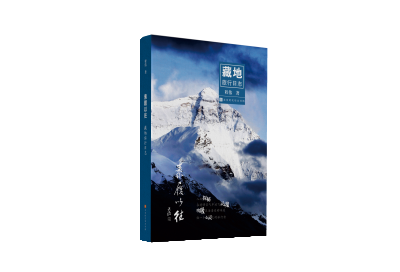
(一)
读程伟新书《素履以往——藏地旅行日志》,仿佛游历了一个人的精神地理、精神风光。
值得尊敬和佩服的人,一定是那种年长依然童心未泯,对世界怀有好奇心,并以积极的性情,去努力探索的人;是那种热爱自然,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心随天地走,勇敢又浪漫的人。
程伟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我习惯叫他老农。在我三十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中,经历过许多人、许多事,到最后能在一起喝杯茶,乃至喝杯酒,讲讲话,随意而亲切的人,他是其中之一。但是,一直以来,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去藏地?好多人不能忍受缺氧带来的不适,去过一次,很难再次出发。而程伟一而再、再而三出发,前后八次,穿越青藏线、川藏线、滇藏线,是什么动力吸引他如此痴迷藏地?读完这本书,我震撼了,感动了。这是一本游记集,以文字、以图片的方式,更是以心灵打开的方式,带给人愉悦的精神享受。
(二)
程伟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西藏产生兴趣的?他在后记中说,第一次去西藏是2004年8月,由于思想上、行动上、文化上没有准备,他跟着导游走,听了解说还是一头雾水。那是一次纯粹的看风景的旅行。回来后他开始查阅资料,这一查,对西藏历史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我注意到,他在书中提到畅销书作家何马的《藏地密码》。我想起来了,这是以西藏文化为背景的小说。它讲述藏传佛教历史遗案以及探险故事,涉及西藏千年秘史及人类对于生死灵魂的看法。这一套书共十册,我问程伟借来读过。那是在2012年,他时任宜兴日报社社长。
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读的书、走的路,决定了他的内心气质。程伟既有激情澎湃、仗剑走天涯的少年气,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气。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作再忙,都要抽出时间来读书。外出时行李里必备书,别人坐高铁坐飞机打瞌睡,他看书。他读的书广而杂,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皆爱读,《藏地密码》这样的系列长篇小说,他也通读。
我阅读《藏地密码》,也就读读罢了,虽然向往西藏绝美的风光、旖旎多彩的文化,可我不敢去,有身体原因,但更多的是心理因素,我缺乏勇气,在乎的东西还是太多。
程伟有可贵的好奇探索心,他看了《藏地密码》,一个强烈的愿望在心底升起:我要去阿里,去探访神秘的古格、象雄、狮泉河……去领略广袤与空旷的自然禀赋,感受浓烈的西部民族风情与文化,暂且远离都市,让身心超然宁静,成为一个心灵上的旅行者。
(三)
一个真正的行者不会依靠旅行社的安排来游览。他每次出发前都要做详细的攻略,了解人文背景,人未入,心先入,这样到了景点,就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打卡式旅行,而是与西藏有心灵呼应。
他捕捉每一处细微的感动。在布达拉宫观看壁画时,他很想看看那位富有情怀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以弥补第一次参观的缺憾。他穿越迷宫般的走廊,“终于在红宫西侧的上师殿找到了那个多情的六世达赖喇嘛的金身塑像。我从密密匝匝游人的缝隙中,看到了他永远年轻的面庞。在管理人员‘快快走动’的要求中慢慢地靠近他,感觉他的脸是那么熟悉,想想,应该是在他的充满深情的诗中读到过。”
这本书非常宝贵的是情景交融、文思兼具。我们跟随他的行走,领略藏地的风光,并通过他的思考,对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有新的知觉。“五世达赖的灵塔最奢华,塔身镶有各种珠宝,极其辉煌壮丽。十三世达赖的灵塔上镶嵌了万余颗珍珠,显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想想也奇怪,既然已经成佛,为何还是这样世俗,既奢华,又华贵。是后人为之,还是佛本来也不能免俗,还是表示他们对人世间的留恋,奢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回来?塔前供奉着长年不灭的酥油灯,空气中弥漫着酥油的芳香。我很快注意到,在供奉的灵塔中,唯独少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那个以情诗名世的活佛……”
很多现代人有个特征,社会性太强,自然性不足,忙于事务疏于大自然。尤其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常常天天和全世界对话,唯独不和自己对话。
程伟一次又一次远行,是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仰望雪山、徜徉湖泊,意味着一次又一次洗礼,赋予生命新的索引,新的知觉、启示与发现。
“寺庙里外没有一棵树,这就是西藏的环境,种活一棵树都很难。但也许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不会为物质拖累,不会为了物质活着。”
2018年这趟旅行十六天,他在日志中随感,我们旅行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找寻曾经失去或者正在迷失的自己吗?脱离惯常的生活场景,甚至生活方式,接近或者深入某种陌生、新奇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净土,人们会生发出意想不到、不同以往的思考,得到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我想,这些对于人们的未来生活及整个人生都是极为宝贵的记忆和财富。
(四)
写这样的书,要具备丰富的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的知识。
阅读程伟写下的文字和途中拍摄的图片,如同跟随他在风光绝美的藏地行走,像我这样没有去过西藏的人,因为看了他的书,比我去亲历一遍感受到的还要多。而到过这些地方的人,都有必要看一遍这本书。
程伟是书法家,他的文字节奏很好,描写有画面感,白描手法,笔调中有宝贵的诚意和随意,极见功力。
“帕羊是风口,特产就是风,风把河道中的沙扬了起来,它们飞舞旋转,最后积沙成山。仔细观察这些由时间堆积出来的沙山,还能辨别出风的方向,它们居然有着惊人的一致。站在帕羊的沙山前,小水塘里倒映着南侧的喜马拉雅山脉,阳光下,那些积满白雪的山头闪亮刺眼,牧羊女正赶着牛羊越过沙丘,往河道深处走去。这里就是中国的最西部。”
这样的文字有筋骨,有血肉。细微的描写将读者带入了场景。
程伟在生活中本身就是这样,细心,有诚意。有次我和徐沭明去看望他,离开时,他送我们出来,站在那里,看我们发动车子,然后举手轻摇、目送。我们忽然心头一热,不是偶然这样,他每次都要送客人出门,然后目送离去。细节中见古意,君子之风,以诚待人。
所以,是什么样的人,就能写什么样的文,他置身藏地的自然与人文,与自己的心达成呼应,又带动了读者。这使得作品既有宏阔的张力,又有幽微的动人之处。
(五)
在空气稀薄的高原,程伟每天写下自己的见闻和感悟,里面精彩的细节如珍珠般滚动。他写这本书是跟自己对话,读者在他的叙述里,会情不自禁地加入对话,或共鸣或引发更多的思考。
他同行的人我大多熟悉,所以读他这本书,不时会心一笑。我看到周旭因高原反应严重,提前退出行程回来。看到另外的同伴在珠峰大本营想抽烟,火柴刮不着,好不容易用打火机点着了一支,但吸了半支已是“男儿气短”……我看到这些就哈哈笑。看到他们路途中遇到恶劣天气,望着没有停止迹象的雨,没有尽头的泥泞路,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塌方、落石,李慧编写了一段发给老公的微信,随时手指一按就可以发出……我就跟着共情,这些小花絮非常有味有趣。
八次藏地探秘,程伟始终是雁群中的“头”,其他的雁是不确定的。这也正如我前面所说,“好多人不能忍受缺氧带来的不适,去过一次,很难再次出发”,而唯有对藏地文化有着无限热爱,一颗探索之心鲜活的人,才会八次前往。岁月给程伟的勋章是丰富的、立体多维的,他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在我写下这篇读后感时,得知程伟又在旅行中,从宜兴驾车前往西藏,日行千里,开车两天后到达成都,并从那里出发进藏。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啊,一个年过花甲的人,生机盎然,带给我们太多的生命感动。
素履以往,以往是少年,以后仍是少年。
【精彩试读】
“在中国,这是一个没有探险的年代,天空波音,地面宝马,功利的眼光左右判断,更重要的是,几千年安于现状的思维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行为。没有探险,但我们不能丧失探险精神,对自然、对自我,我们都希望过上舒适、甜蜜的生活,可现实的生活是充满酸甜苦辣的,如果我们只知道甜,那说明你的生活是不全面的,是存在了缺憾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篇
“藏人们对内心的索求,一定远远大于对现实的索求。也许藏人们在磕长头中,悟出了‘现时’的虚无性,从而花毕生的精力去追求‘来世’。”
——“行走香巴拉”篇
“回程是下坡,马的脚在打滑,腿也似乎在打颤,鼻子喷着粗气,我坐在马背上感觉很不踏实。可我们又能怎样?我还是坚信马的能力,我们既然相信了马,就把自己的安危交给了马。骑在前仰后合的马背上,我不禁感叹,人还是要有点把自己交出去的勇气,也要有信心、信任的勇气,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
——“行走香巴拉”篇
“随着尧茂书和多名漂流勇士遇难,人们在痛定思痛后也曾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这是高尚的爱国主义,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这是‘无畏的’牺牲,还是‘无谓的’牺牲?尧茂书他们逝者已逝,‘名’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但他们那‘最后的伟大征服’,我以为,更是为了寻找一个精神突破口。当一个民族在经历了长久的压抑和屈辱后,渴望有一种方式来释放和宣示自己的力量,以一种不甘屈辱的形象站在世界面前。当一个民族奋发图强时,也需要去寻找源头的洪荒之力。这在长江漂流与中国女排身上体现了,长江漂完全程,中国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并称为当时中华民族的两支精神催化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同样的拼搏点燃了那一代人的梦想和激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成为那一代人的化身。”
——“行走香巴拉”篇
“在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们总被一种神圣震慑,没有喘息的机会。你会感觉到天地之间所有的东西无不神奇而圣洁,你会将过去所经的一切烦恼一下子全部忘记,你会觉得不管多大的烦忧在这伟大而神圣的女神面前都不值一提,不值一顾,微不足道。”
——“阳光与荒原”篇
“此一刻我忽然感到珠峰上的流云如同时间,在匆匆飘过的时候,我像站在了一个超越时间的高度,审视着沧海桑田之后所留下的永恒。那一刻我是宁静的,只与时间对峙,与永恒比肩。其实我们所有人和事都是匆匆过客,只有我们的意识才能超越时间的概念。”
——“阳光与荒原”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