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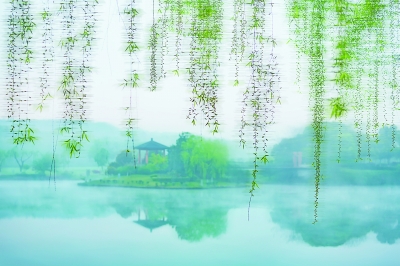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方阳羡田。
和脱胎于陶渊明笔下成为无数中国人精神故乡的“桃花源”一样,“阳羡田”也是一个专门用语。词典网解释:“阳羡田,源见‘买田阳羡’,借指归隐之地。”
“百世春秋传,一丘阳羡田”……千百年来,“阳羡田”出现在无数诗文中,成为人们向往的精神家园。历代更有文人雅士心慕身追,更籍或迁居宜兴,为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和持久的活力。
前见古人: 闻而慕之的移居
宜兴东依太湖,南接天目,自古就是山水清丽、人文蔚起之地。旧志记载:“铜官、南岳之耸拔,蜀山、蛟桥之胜迹,张公、玉女之灵异,往往闻而慕之。”翻开历史,在东坡之前,就有这样一批批的身影来到阳羡,追寻心中的山川田野。
所谓“闻而慕之”,即听说此地灵山秀水于是心生向往,移居者络绎不绝。有史料可寻的最早迁寓宜兴的是上古高士善卷。《庄子·让王》记载“舜以天下让善卷”,但善卷坚辞不受,于是一路南下,最终在四季皆景、杂花生树的张渚螺岩山中驻留,安贫乐道地过着“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生活,成为中国隐士第一人,也让宜兴在隐逸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善卷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宜兴也吸引着文人雅士们。梁代山东寿光人任昉在宜兴任太守,留下了卓然政绩和游寓佳话。他酷爱阳羡山水人文,因常垂钓于西氿之滨而留有“任公钓台”;建寓墅于画溪北岸,丁蜀“任墅”村名由此而得;为方便百姓出行建造了以其字为名的“彦升桥”。他的好友到溉、到洽兄弟受其影响从彭城迁居查林村,一起吟诗歌赋,交游唱和,将君子理想融进了异乡的土地。这些村庄、小桥、钓台历经1500多年风雨,依旧可以寻觅它们当初的身影。
时间来到盛唐时期,江南勃兴,迎来了文人雅士迁寓宜兴的一个高峰时代,一时之间,阳羡大地大咖云集。诗人杜牧把在阳羡置业一事以诗题《李侍郎于阳羡里富有泉石 牧亦于阳羡粗有薄产》形式昭告亲友,喜悦而自得。“终南山下抛泉洞,阳羡溪中买钓船”,和友人叙旧述怀,相约悠游,东氿畔的“牧之水榭”承载了诗人对生活的向往。唐朝宰相陆希声学识渊博,颇有清名。政事蹉跎中,他独对阳羡山水流连忘返,来宜兴隐居后,遍历清溪幽壑,除了湖㳇颐山的陆相山房,还在铜官山的君阳洞小住,“君阳山下足春风,满谷仙桃照水红”,自号“君阳遁叟”。《全唐诗》共收录了陆希声所作的《阳羡杂咏》《山居即事》22首诗,篇篇都是描绘宜兴山水风光之作。被称为“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长卿曾被诬罢官,去职后当即来到宜兴,建造“碧涧别墅”寓居了下来。宦海沉浮中,阳羡是他心中的秘境,无论顺流逆流都可以安放漂泊的灵魂,那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不知道是否是他彼时的心境?
“山水之胜在吴,宜邑又吴中最胜”,高度人文化的秀丽风光成为文人们创作的源泉和归依的家园。穿过时光的河流,无数名臣雅士把阳羡作为家园故土,他们在此耕山钓湖,遂心物外。我们看见唐朝名士皇甫冉、宰相权德舆、滁州刺史李幼卿、常州刺史独孤及皆寄寓于此。诗人谢灵运、李商隐、李绅也在阳羡山水间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这些外邑名家舟车往来,唱酬不断,在宜兴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文坛盛会。这已不仅仅为倾慕自然景观,更多的是寄意精神之交流、同气以相求了。阳羡山水滋养了寓客,他们也反哺了这块土地,参与和兴起文化活动,创造诸多文学作品,极大程度推进了宜兴人文蒸郁和文化兴盛,不仅为溪壑增色,也让“敏于习文”成为阳羡的文化标识之一。
值得探讨的是,历史上“地偏俗俭”的宜兴为什么能让名士巨擘们“闻而慕之”纷至沓来?这与地域人文性格不无关系。《寰宇记》称宜兴民俗“人性佶直,黎庶淳逊”,宜兴不在当时的国道运河边上,也远隔通都大邑,逐渐形成了山地丘陵形“佶直”心性。宜兴地貌丰富,物产丰饶,千百年间人才辈出,“淳逊”之风自成一脉。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契合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选择。这样一个山川灵秀、民风质朴之地自然而然成为进退皆可的理想家园,蓄积兼济天下的志气骨力,播植归老田园的清娱梦想。
后有来者:
买田阳羡的效仿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宜兴买田置业,经朝廷允准就此居住。可惜东坡先生宦海沉浮,几经贬谪,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数十年九死一生的颠沛流离中,阳羡田园梦温暖了他无数黑暗无助的长夜。北宋以后,外邑名宦巨擘纷纷仿效东坡,接踵而至,将东坡没能达成的田园梦从理想变为现实。
因名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而被称为“贺梅子”的词人贺铸多次来到宜兴,求田问舍、渔溪樵山的生活让他向往和羡慕,他把《踏莎行》的词牌改为《阳羡歌》,“山秀芙蓉,溪明罨画”,浩歌清曲穿越时空传唱至今。去世后,贺铸没有回到故土河南,而是埋葬在宜兴城南的筿岭,阳羡青山绿水里安放了他耿介长情的灵魂。
南宋名相周必大是宜兴的女婿,两任妻子都是宜兴人,长期寓居宜兴。任职期间也常来宜兴小住,他在《跋东坡楚颂帖》中写道:“余自绍兴癸酉(公元1153年),迄淳熙己酉(公元1189年)三十七年之间,凡六至宜兴。”他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描绘此间风物名胜、人文历史的佳作名篇,《胜果寺咏阳羡茶泉》就是其中之一。两宋之际,达官贵人纷至沓来,蔚为大观。首次刻印《世说新语》的董弅也来到宜兴寓居,他在溪涧上筑建了楚颂亭,以遂苏东坡未竟之志。大理少卿王葆因疾致仕向朝廷请归宜兴,他潜心学问,教导后生,李衡、周必大、范成大等来到阳羡投其门下,皆成一代名臣。名臣李纲未第时读书于善卷寺,罢相谪官后再次流寓阳羡。
青果巷是常州名巷,“一条青果巷,半部常州史”,先后走出百余位进士及名人,明代大家唐顺之和唐氏家族曾经的荣耀都藏在这条街上,成为青果巷的灵魂。唐顺之会试名列榜首,这位文武兼备首提“唐宋八大家”的江南才俊领军文坛,大破倭寇战功赫赫,但却因触怒权臣而遭罢谪。离开朝廷南归,壮志未酬的他没有回常州老家,而是在阳羡山中开启了十多年的家居岁月,这一方土地让唐顺之心安。史称他因“雅意荆溪山水”而仿效苏东坡取号“荆川先生”,从此,一个具有东坡心性的唐荆川出现了,以孤忠亮节、文采风流傲然于世。他开馆授徒、课子研学,虽幽居乡野,却声名更盛,乡绅布衣、贤才高士鱼贯而来从其学,宜兴礼部尚书万士和就是其中一位,僻静的山林引发了阳羡文化的磁场效应。日后,唐顺之重被启用,成为一代贤相名将。
万历年间吏部右侍郎徐显卿本是苏州人士,因言官攻讦请求致仕,携家定居于宜兴长桥东隅,从此苏州徐氏一脉在宜兴开枝散叶。徐显卿晚年曾请画师将其一生际遇作成《徐显卿宦迹图》,他逐张亲题咏记,现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第十四幅“荆岳卧病”就是讲述其抱病领命前往湖北,完成使命后未回北京,而是请了长假返回宜兴治病休养的场景,在徐显卿心中,宜兴已俨然成为故乡。值得一提的还有明朝重臣、“茶陵诗派”核心人物李东阳在宜兴买田欲居,他在《苏文忠公祠堂记》中说自己是楚国人,生于燕京,但却在江南宜兴买了田,后因罹患家难,和东坡一样成未竟之志,不由感慨万分。于是当同僚好友宜兴籍内阁首辅徐溥请他为东坡祠堂作记时,他有感而发,用家乡楚语作了迎送神辞,竟《楚颂》遗意。这块石碑现在还完整地保存在蜀山东坡书院。
追随东坡起意买田阳羡者不胜枚举,越来越多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寄情山水,志定心安,明清时代迁寓达到了鼎盛。“此中如有田堪买,好似东坡学养生”,明朝内阁首辅徐有贞孜孜以求在此买田,陕西布政使杨守鲁致仕后买田阳羡为终老计,武进人龚胜玉慕苏东坡而卜居宜兴,绘《仿橘图》以明志……
如果说东坡之前是游寓宜兴为多,用今天的话语说是“流动人口”,那么东坡买田阳羡就标志着将全部身家留在宜兴,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户籍人口了。这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地理背景,即在北宋中后期开始,经济社会逐步由南北并重而到南方为主,政治中心也一时南移,宜兴作为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却相对开放的所在,无疑给仁人志士提供了一个栖心栖身之所。买田阳羡已然成为人们表达精神追求以及生活态度的一种固定模式。传统的士大夫情怀从精神层面化为具体行动和现实体验,这不是消极意义的避世,而是在特定现实社会背景下的一种选择,是振翅待飞的入世追求。
身为心留:
东坡精神的内核影响
尽管阳羡之梦最终伴随着苏东坡北归染疴而病逝常州戛然而止,但他的独立人格和积极精神已永驻阳羡的山川大地,也在这片罨画溪山播下了“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精神种子。
苏东坡一生流离,足迹遍及四海,但宜兴无疑是他真正的第二故乡。宜兴百姓也把苏东坡当成了本土贤达,将其安放在了乡贤祠世代供奉。历史上,每至其诞辰,无论官员还是乡民都会到东坡书院(原为东坡祠)进行祭祀。东坡精神通过在阳羡买园种橘、拟建“楚颂亭”而具象化,这也深刻地影响着宜兴人文的衍变走向,成为这方地域最具特质的传统精神和最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潜移默化地润泽着一代又一代的宜兴百姓。
本籍历史上第一个辉耀今古的词人“樱桃进士”蒋捷,身经南宋沦亡、家国易主之痛,抱节而归于家乡周铁竺山。在那首著名的《梅花引·荆溪阻雪》中,他写道:“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这是词人内心的拷问,隐居不仕并非本意,只是山河崩析之际若不能力挽狂澜,那就独善其身吧。这无疑是蒋捷对东坡精神的一脉承继,守志独立,心安乐道,其清逸情韵和高士品格也成为大家对阳羡文人的普遍认同,流风余韵影响至今。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遭遇迫害而屏居故里,在家国危亡之时,他“濒死而不悔”,蛰伏于滆湖之畔的亳村,十多年足迹不入城市,“遗民故老时时犹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身在朝野心念时局,他所坐卧的小楼成为“惊离吊往”的集合点。乱世之中抱朴守志受命不迁,这是对品行节操的坚持,是对自我价值的清醒追求,更是东坡精神的延续。
深受影响最浓墨重彩的当属以宜兴籍词人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词派”。值得探讨的是,在清初词学振起之际,宜兴何以以区区一邑的地域群落,会聚词人上百位之多,有宗师,有群体,有理论主张,蔚为大观,成为中兴清词贡献最大、成果最丰硕的一支流派呢?而且,创作题材和风格有着鲜明的本土特点,寄情山水、托物明志,抒家国,系民生,豪逸疏狂、情思绵渺,延续了东坡词的神韵。不能不说,这与东坡精神滋养下历史人文的地域积淀,有着深层的不容轻忽的关联。自号“枫隐”的吴洪裕,举于乡但不复赴会试,饮酒吟诗,雅集聚会,名人王稚登、董其昌皆从其来阳羡游。本土名臣吴载阶、吴璇、徐喈凤……尽管境遇各不相同,但面对家国动荡、壮志难酬时,几乎都做出了相似的选择,弃仕归乡,度己及人。
直至今天,在吴越城市圈中,宜兴的城市气质呈现着迥异的个性特点,与江南文化的婉约柔和相比,更多了一分刚直硬朗、淳厚朴实。东坡心性已融入世代百姓的血液中,成为宜兴地域最具特色的乡土特质。与之相应的是,宜兴本土人才在东坡精神为代表的文化浇灌下,双向奔赴,建构起更为宏大的东坡精神,田是外形,精神才是不灭的。现代宜兴赓续着科技、教育、艺术等领域的辉煌,代有一心爱国、以身报国的栋梁之士,无疑是东坡精神浸润下的源远流长。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千年前东坡的夙愿早已在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落地生根,又在一代又一代文人才子、百姓士民的心中开花结果,更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身为忙碌的现代人,或许买田耕种的愿望显得有些遥远而不切实际,但我们不妨学着在复杂多变的世情中秉持乐观豁达、坚韧积极的东坡精神。正所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愿每个人都拥有一方自己心中的阳羡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