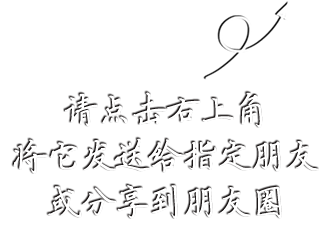“在路上”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为你无法洞察下一秒究竟是惊喜还是失望,正如车窗重复上映绿意时,忽然铺满金灿灿的油菜花;眼眸还未来得及收拢花苞间的微光,就被呼啸而过的黑占领了视线。雀跃的电子音提示到站,我推了推旁边打鼾的兄弟们,这趟毕业旅行,由三张揉皱的车票,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开始了。
和印象里的古城不一样,这里没有优雅的楼阁与亭园,有的尽是烟火气。深红色的砖瓦间,有百叶窗扑动着过往,我看到每一处屋檐下,都有孩童盘在老人腿上,听着远去的故事。此前早有耳闻,来福建漳州不品一品“四果汤”,便是虚度。它虽谓“四果汤”,但小料近乎十来种,掺有蜂蜜的糖水一淋入,那些上浮的果子就像饱腹后胀起的肚皮,是让人心安的满足。酒足饭饱后,我们倚在冷清的天桥上,望着夜色坠落,涌动的车流汇入各自的归处,只剩不确定的未来,还在迷惑着我们的年轻。是继续升学,还是成为人海中仓促的一抹?我们的脸上,依旧悬着相似的彷徨。
次日,我们来到期待已久的东山岛,海风细碎的耳语披在肩膀上,招呼着脚步向前去。只是落脚的轻重必须拿捏,因为茫茫沙砾中总有几只筑巢的小螃蟹,用捏紧的爪子,警惕着忽然落下的脚印。也许我们追逐浪花的时候,浪花也在追逐我们,只是有时候追海不一定是为了落日,也可能是为了飘远的拖鞋。上岸后,听说远处有座苏峰山,可以俯瞰整座岛的美景,我们会心一瞥,导航一定,两辆电车便载满笑靥远去。可由于我们体重分配不均,未至半山腰,车子已是走两步歇三步,发出“嗡嗡”的悲鸣来。两个同伴又是哈气,又是抹汗,几个人轮流坐上“宝马”又换下,几近放弃。终于,在历经一个满是凸点的斜坡后,我们一起坐在那倦怠的“马鞍”上,望着落日缓缓从山间的薄雾中“孵出”,云层透出的光仿佛眉间苍老的皱纹,宁静而慈祥。我瞄了眼身边的同伴,他们的瞳孔中都跌撞着久违的温热。
归去的途中,大巴车被疲倦淹没,没有一处喧嚣绽开,人们的鼾声整齐得像一首安眠曲。我把手臂贴在窗上当靠枕,正打算融入这合奏时,忽然瞥见旁边的男孩,借着昏暗的光,勾勒画上的色彩。虽然那耷拉的脑袋总让视线模糊、线条歪斜,可那握紧的小手却从未离开笔尖,每次落笔,纸张上就多了一处皱褶。终于,他脸上的疲态已难以抗拒,缓缓倒向我肩膀。我看见他的画纸上装着另一个小男孩,在博物馆里展示着标有“待定”的画作,题名为:梦想。这让我的心头止不住地颤动,曾经,我遥望着寄托在文字里的梦,却因投稿长期石沉大海,逐步陷入否定,不再提笔而抒。可被我遗忘的,是那伏案在无数个透不出白光的窗前,用文字描摹出月的倩影的少年。世界是个容易迷失的丛林,走得久了,就会忘记来时的记号。如今,我处在毕业的岔口,孤伶地对抗着拥挤的虚无。只是,我依然有梦、依然有胸口沸腾的呐喊,这些微小的文字,足够我在泥泞的远方,种下一棵待放的绝色。
在挥手道别的片刻,那些积累的怀念,是我们没有说出口的沉重。面对愈重的行囊、微茫的未来,我们唯一的确信,是永远在路上。也许,在人世间跌撞着探索远方,本就算得上一种美丽的答案。(李治橦)